隆冬蓝山记
2021-01-14摘自《自然物语丛书(第三辑)》之《野林之路》原文地址
隆冬蓝山记
文/【美】温思罗普·帕卡德
译/董继平
接近早晨,那南方之雨停了,它那倾盆的降水量成为 1 月雪融的高潮,在那追随大蓝山(Great Blue Hill)的温暖的沉寂中,那山冈似乎像一朵巨大的马勃菌(puffball),从潮湿的薄暮生长到黎明时更干燥的上层大气之中。伫立在它那球状的圆顶上,你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因为它而受到了向上和向东的摇摆,去迎接光芒。在这样的时候,地球围绕其轴心的旋转就变得如此真实了,使得你想知道古人很久以前伫立在山顶上是否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他们当中的登山者肯定是知道的。
过了一会儿,天文台那带有垛口的城堡主楼就越来越清晰,赫然逼近,你开始注意到脚下灰白的泥土的其他细节。南风吹过来,给你短暂地带来并留下百慕大群岛(the Bermudas)的空气,你只需要凭借鸟鸣快乐的吵闹,就认为此时是 6 月,而不是 1 月。相反,这里有一种毫无声息的沉寂,它融为一体。破晓时,在金色光辉中呼吸这种柔和的空气,似乎这座山冈的整个顶部都保持着沉默。它知道。
当白昼渐渐明亮起来, 你就能看见那些小小的胭脂栎(scrub-oak)簇拥着丛生,它们把顶峰的高地变成了自己的家园,让自己蜷缩、安顿在一起,接受那冬天命运的耐力考验。就在南方之雨持续之际,它们对其敞开了心怀,但它们知道在雨水消失的那一刻,自己要期待什么。早在想起天文台之前,它们就从蓝山顶上研究过天气情况。
所有的树木都热爱山冈,但只有极少数树木才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才能忍受冬天时山冈的严酷环境。你能看见山核桃和铅笔柏(red cedar)从四面八方群集着,渐渐爬上陡峭之处,而就在你注意胭脂栎怎样让自己变得紧凑之际,你还会看见那些铅笔柏占据了岩石边缘,就像在因克尔曼(Inkermann)战役中,那排成细细的红色队列的苏格兰高地居民。它们全都因为不懈的努力斗争而变得矮小、残废,一直到它们似乎与冲积平原上那些快活、纤细而轻快的铅笔柏相去甚远。你能清楚地看见它们在这里咬紧牙关,坚持不懈地生长。
然而,它们热爱自己紧紧地把握了好几百年的岩石,但遗憾的是,死亡最终会分开它们。在蓝山的南缘附近,有一些铅笔柏从灰白的花岗岩中长出来,这让我想起,当巴塞洛缪·苟思纳(Bartholomew Gosnold)——这个涉足马萨诸塞土地的第一个英国人踏上海岸的时候,它们就在那里了。这样的时代,不属于那些在高地边缘上设法高出一头的山核桃,然而它们也丧失了自己身子的苗条。寒意和山顶的风常年压制着它们,最终把它们变成那种身子粗短的大头矮树。
如果我们从山底开始,我们就会更了解其他树木究竟是怎样攀登这座山冈的。相比其他的日子,这一天更能让我们仔细地查看它们的情况,因为南方之雨扫走了所有的积雪,让地面裸露出来,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里的气温属于南北卡罗来纳,而不是拉布拉多,因而成为我们在1月通常会经历的一部分。确实,阳光明媚的平原从南部的岩石斜坡底部伸展开去,从那里,你能看见那些纤弱而欢乐的植物,看见它们最活泼地向上攀登之处。
黄色的假毛地黄(gerardia)显得很健壮,其中一些高达 1.8 米,在那肥沃的黑色腐殖土中生长,而那些腐殖土则穿过乱石堆,一路向上迈步、铺展。从 8 月开始到霜降初次侵染它们的这段时间里,它们一直在山核桃、栗树、枫树和白栎(white oak)下面扩散着阳光,似乎将其从金色的碗里倾泻出来,打碎成那随之而来的秋麒麟草的花朵的薄雾。尽管这些假毛地黄已经干枯了,但在整个冬天,任凭强劲的大风吹击和深厚的积雪覆盖,它们都无畏地伫立着,勇敢地高举着它们那褐色的种子荚,在凛冽刺骨的大风中,那些种子荚露齿微笑,散发出它们那糠一般的微小的种子,让其高高地飘浮到山坡上面的不远之处。很多个世纪以来,它们都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任劳任怨,但是,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攀登得很远,然而它们如此热爱这座山冈,因此它们顽强地依附在自己占据的地面上——相比在不那么崎岖、粗糙的土壤上,它们在那里生长得更加旺盛。
这座山冈上,最粗糙的突岩朝着南方醒目地突出,对着太阳露出花岗岩的侧翼,使得这一边几乎完全成了岩石峭壁。然而在这里,高地的铅笔柏却选择了以大批行动的方式向上攀登,用赤褐色和橄榄绿来呈现出彩色的格子状,在那些似乎只有气生植物才可能找到的营养物之处,它们凭借脚尖而顽强地依附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山岭的斜坡稍有崩溃,只要它们赋予黑色土壤更好的立足点,山核桃就会生长在铅笔柏的侧面,但其他树木都小心翼翼,不敢这样生长在光秃秃的花岗岩峭壁上。
说来也奇怪,随着山核桃一路向上,那些紫色的林地禾草(wood-grass)也派遣出侦查小队到处出击,它们肯定最热爱多沙的平原。但在这里,它们却渐渐向上攀登,从而占据了突岩间那些微小的高地,朝着山岭而涌现,其边缘则常常围绕着山蔓越橘(mountain cranberry)呈现出略带紫色的绿色。在冲沟底部,枫树开始攀登,然而它们并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赤栎(red oak)和白栎赢得了更高远的地位,却总是在抵达冲沟顶峰之前就停下了脚步。
靠近蓝山顶峰高地的东部界线,从美丽的艾略特纪念桥(Eliot Memorial Bridge)上,从一条狭窄的沟壑朝东南方俯视到一条宽阔的山谷,你可以瞥见奇妙的景色,从那里再看到一种白冰的光亮,那即是霍顿湖(Houghton'sPond)发出来的。你看见,光秃秃的树木不再相互掩藏,却大规模地进行侧翼运动,朝顶峰挺进,在更为宽阔的高地山谷中群集,收缩成巨大的栗树群对着冲沟上面疯狂地冲击。这些栗树似乎不曾根深蒂固地伫立,它们左摇右晃,似乎在疯狂的激动中欢呼、挥舞旗帜,在绝望又充满希望地冒险。当然,它们一动不动,但完全就像天才人物赋予雕塑的那种壮观的步态,给山岭上风景优美的地点增添了传奇。然而,从来没有一棵栗树把自己的顶端高高地托举起来,超过冲沟的山岭。它们满怀周密计划和协同作战的美好热情,朝着山岭一步步推进而来,却如此突然地止步了,以至于你依然看见它们迈着壮观的步态,仿佛一只脚还停留在空中,寻找那应该把它们带到山岭之上的阶梯。
就这样,长期劲吹的北风把它们阻止在那里,把它们的顶端阻止在山岭边缘的水平面之上够远的地方,从而让它们免遭北风不断吹击带来的伤害。你最清晰地看见,它们一步步爬下那道小小的冲沟,来到那些生长于岩石间最潮湿的沃土中的鳞毛蕨(evergreen wood fern)中间,那可是唯一的绿色痕迹,除非你碰巧遇见某些瓦苇——似乎是从岩石本身长出来的瓦苇,情况才有所改变。
就在栗树中间,随着树林那小丑般的魔术,外貌再度发生了变化。正如你从上面看见它们的那样,那些大树不再固定于那种朝着壁垒不顾一切地拼死冲锋的姿态中。在它们当中,它们似乎是喝得醉醺醺的酒徒,选择了这条隐蔽的小峡谷作为狂欢之地,就像是笨拙的伐木者围绕着小峡谷而旋转,跳起大脚舞。一棵独自伫立在平原上的栗树,外貌犹如乡村族长一样庄重而威严,而在这里,栗树们一起簇拥在平坦、肥沃的林地里面,整洁而又几乎像贵妇一样雍容尔雅。在蓝山顶峰东边的小峡谷中,为什么这些树会在笨拙的骚动中跳跃,我不得而知,也无法述说,但是它们似乎的确呈现出这样的姿态,而且,我还不是唯一见过这种场景并为之震惊的人。
就在附近,生长着一群山毛榉(beech),它们犹如女学生一般,身材非常笔直而苗条,皮肤白皙而暗淡。这些树木靠在一起,颤栗着聚集成一群,显示出女性尊严的征兆,非常年轻而又相当蛮横。它们窃窃私语,尽力让自己显得高挺而又非常纤细,早在你抵达它们之前,你在大老远就能听到它们的嗓音发出那种愤慨而干燥的裁剪之声。无疑,它们想让整个峡谷都属于自己,在此进行适当的野餐,在野餐上享用洋李干和泡菜。在这里,这些伟大的伙伴行为如此不端,这是一件羞耻之事,公园警察应该出来予以制止。在它们愤怒的撤退中,这些山毛榉如此地结上冰霜,使得它们的枯叶发出冰冷的低语,听起来就像是迅速下落的冰雨。当你在山上临近,在它们中间悄悄移动,你就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吧。这一天可能就像一个冬日那样,阳光明媚而温暖,但是你会认为自己听见了雪花迅速飘落,还会遗憾自己不曾戴上皮毛围巾来保暖。
至于那些栗树,我怀疑它们依然在冲沟下面的寂静中非法畅饮山露。确实,在这条花岗岩山脉的顶端中间,泉水是不可能喷涌出来的。然而,在大蓝山和汉科克(Hancock)更小的山嘴中间,泉水可以自由自在地喷涌而出,它们的湿气是从小湖凉爽的深处吸取来的。南方的太阳照射到那些小湖之中,北风和西风被花岗岩山岭挡了回去,如此一来,这些湿气就成全了各种树林生物和牧草地生物——它们渴望不断攀上山峦的高处,为它们进行拉力赛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它们却无法忍受顶峰严酷的环境。在这条山脉的高处,这样的小湖共有 3 个,相互距离几乎只有一箭之遥。水从周围的突岩渗出来,这可能说明了它们的水流,但是我更倾向于,正是那些隐藏在山冈脊椎里的裂缝,能让水从地下深处涌到地表。两个小湖的边缘,成了一簇簇绿蔷薇(greenbrier)快乐的家园,它们犹如繁茂的热带植物环绕着小湖而蓬勃地生长,用多刺的缠绕物将灌木丛束缚在一起,因此,如果要穿越这些缠绕物而前往水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美国梧桐(buttonball)和高丛越橘(high-bush blueberry)随着它而生长,伸出一根根枝条,作为它那菝葜(smilax)一般的装饰物;庄重而秘密的金缕梅(witch-hazel)在这里沉思冥想,四处潜行,无论在何处,只要头上的叶簇很浓密,足以构成它最喜爱的那种神秘的微光,都有它的身影存在。它在栗树的阴影下漫步爬上冲沟,你只能这样想象:对着那些女学生般的山毛榉的狂欢及其一本正经的愤慨,它露出了讽刺的微笑。很奇怪的是,那些红花槭(swamp maple)不适于伫立在山顶,当你伫立在它们下面,它们就会在黄昏中到处闪烁起灰色的光亮,要不然,当你从悬崖上看着它们的枝条末梢,它们的面颊就在明媚的阳光下泛红。这是一座风景如画、拥有 3 个小山嘴的山峰,位于大蓝山和汉科克之间,尽管那些小湖上的冰层洁白、坚固而结实,但在正午的阳光下,它受到了如此的庇护,又如此温暖,因此你只有通过观察天空,才知道现在是冬季。
我认为,从那些悬垂于霍顿湖上的山嘴和湖泊那边,从汉科克之南更小的山冈顶峰上,你才能获得欣赏大蓝山最佳的视野。在那里,你看见森林覆盖的山坡宏伟地扫掠上去,从而形成这个宽阔的高地山谷,在那 3 个小湖所在之处带着褶皱而稍稍形成了皱纹,然后再度沿着这座山冈陡峭的侧边升起来,那种形象最为庄严。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这里展现出一大群宽阔、庄严而光秃秃的树干的灰白色,在其中,岩石山岭朦胧、模糊地伫立在更纯粹的色彩之中,而与此同时,到处都有大片大片簇拥的细枝让它呈现出紫色。你看得见崖壁上的黑色阴影——那条小峡谷就在那里,栗树就在小峡谷中尽情地玩乐。在下面,靠近那 3 个小湖最高的那个湖泊,微微溅洒着一道美丽的白色,其中又完全充斥着粉红色。这体现了一群年轻桦树生长的位置——在这条山脉的高处,它们可是稀罕之物,是我发现的仅有的桦树。
正午逝去了,南风为我们带来的那种亲切的温暖也随之而去。北方的微风没有嬉戏、喧闹,它们里面却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气味,撕碎了那些在大蓝山顶峰之上迅疾地飘进视野的云朵,推动深蓝色的影子越过风景呈现的温暖的灰白色。在这条山脉的每一座顶峰上,太阳和风在继续进行古老的战役,互有胜负。攀登汉科克的南坡,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冬天。你可以随意选择,在高地的顶部左右逢源,让自己置身于两个季节中的任何一个季节,然而伫立在悬崖边缘,你毫不怀疑那道悬崖面向北方。在这个方向,从你的脚下一直到山脚,的的确确是冬天。然而,这里有整条山脉上最翠绿的地点。于是,我不顾危险,攀援着爬下崖壁,用双手触及浓郁的绿色植被,来到崖底,伫立在茂盛的植物中。因为在这里,你就来到了蕨类植物的聚会之地。
崖壁处于一个仲夏日子的正午,细微的阳光触及这道崖壁。整个冬天,光线都没有直射着触及它,然而在寒冷的薄暮,瓦苇一直沿着山岭的顶峰而群集、簇拥,滴落着、舞蹈着蔓延下来,朝着邻近的蕨类植物伸出手——为了迎接它们,那些蕨类从下面潮湿的阴影中欢乐地爬上来。那些蕨是鳞毛蕨。在较低的林地冻结的黑色沃土中,它们茂盛地生长。在向上延伸的岩石嶙峋的斜坡上面,它们抓住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突出之角,不断铺展它们浓郁的绿色,使得灰色岩石的格子状和褐色的叶片显得斑驳。在悬崖与乱石堆相遇之处,这两种蕨类植物结合,亲如兄弟,瓦苇与我经常见过的不同,此时它们距离悬崖更远,而鳞毛蕨则生长在岩缝中,那些岩缝则比我所知的任何地方都要纤细、光秃。
从汉科克返回大蓝山的途中,太阳从所有小小的沟壑中消失了,在我刚刚离开的那道悬崖上,蕨类植物结成花的阴影透露出了寒意,似乎一直伴随我而行。小小的冲沟里面,特别黑暗而又寒冷,我抵达这座大山冈顶峰时已经太晚,已然看不见太阳了。那里,拂晓呼出春天的气息之地,夜幕在冬天之风的撕咬中不断颤栗。上百万次电光的闪烁朝着北方撕裂开了紫色的黄昏,但是,即便是在那些闪烁融合到城市光亮之中的时候,它们里面也没有一丝温暖。随着夜晚的阴影,冬天残忍的把握力压制了山顶,正如我了解了早晨金色的光辉一样,我也再度了解了这是隆冬。那些被暴风雨变得坚韧的矮小灌木丛,似乎稍稍更靠近那异常坚硬的泥土而蹲伏着,它们那被霜降冻得僵直的细枝,在凛冽刺骨的北风中歌唱。此时,我感到了彻骨的寒意,便渴望踏着响亮的花岗岩,走上回家的路。
摘自《自然物语丛书(第三辑)》之《野林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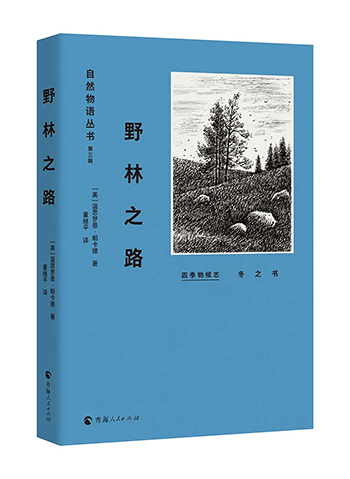
热门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