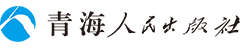吐谷浑国地理考释
2019-06-06《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原文地址
吐谷浑国地理考释
文/李文实
( 一)吐谷浑先后活动地域
吐谷浑早期活动地域,根据《晋书》《北史》及《梁书》等有关记载,先以洮河流域为中心,东至甘松(宕昌),南界龙涸(松潘)、昂城(阿坝)。继向西南发展,奄有河南赐支河曲(今青海黄南、海南两州地区),更南极于白兰 (今青海果洛州地区),西北极于且末、鄯善、于阗(今新疆东南部),甚至曾一度南到罽宾 (今阿富汗)。到唐初其势力分为两部:东部以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石乃亥 )为中心;西部以鄯善(今新疆若羌地区)为中心。最后因受吐蕃进迫,退到西平郡(今湟水中游地区)附唐,再转徙河西走廊,更迁灵州,以后趋于灭亡。其部族大部均为吐蕃所并。
吐谷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幅员东西达三千里,南北达一千多里,实际上是役属群羌,并先后与前凉、前秦、南凉、西秦及北魏、西魏等割据政权属地交错,兼与江左宋、齐、梁政权通贡使;到了隋唐,则更与其所建置郡、县以及吐蕃统治势力相消长,并非真正长期统一的国家。其政治中心早期在洮河流域,中期在河南地,后期在青海湖周围。经过近代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研究与考察,上述情况,已明确一致。惟尚有一些地理上的问题,则言人人殊,出入颇大,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出版),也不免如此,因此尚有必要继续加以探索。
( 二)对吐谷浑几个地名所在的考察
1. 白兰:1950 年夏,客居顾颉刚先生沪寓,常与先生谈论西北古代舆地。某次,先生询及白兰地望,当就所知草《白兰地望考》一文呈览,断其地在今巴颜喀拉山之阳,说为先生所采(见《史林杂识初编》)。前年写《读<青海地方史略 >琐议》,据先生所论,更有所补充。
白兰为白兰羌所在地,是群羌居白兰地区的一大部落,长期为吐谷浑所役属,且一直为其经营东西及退保的重要战略地带。关于这一地带,除了顾先生所论证和我前所补充外,近来细检有关正史记载,发现尚可从其他方面证实其地的明确所在,特再论证如次。
《南齐书·河南氐羌传》云:
(吐谷浑)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砂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瘴气,使人断气。
又,《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亦云:
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屈真川有盐池,甘谷岭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岭,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兰土出黄金铜铁。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
在以上两段记载中,都提到吐谷浑河南居地及白兰都有“雀鼠同穴”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是奇异的现象。这种动植物生态,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动物所适应的地理环境,实有助于考察其地区的所在。
雀鼠同穴这一动物生态现象与植物生态所呈现的黄紫花草,构成吐谷浑与白兰羌所在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而今之大积石山地区,仍有这种动植物生态存在,恰能说明白兰羌所在地与吐谷浑政治中心赐支河曲地理环境完全相同,用知其地即在大积石山范围内,而并不如近人所说在今柴达木盆地之中。(《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魏晋南北朝部分中,标其所在于今都兰至格尔木区域内,而在隋唐部分中却又标其地于今果洛州地区内,前后显不一致;据闻有些东邦学者的考证,也与此相同 )
《南齐书》和《宋书》的记载,都偏指吐谷浑活动中心在赐支河曲(河南地 )时的情况而言。吐谷浑在此时期内,凡遇到从东、北两方面来的袭击而不能抵抗时,则辄退保白兰以自固,是其地在河西九曲之南,而不在其西北。《周书·异域传 (上)》云:
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 ( 郍)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
( 郍)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
这里所谓其地东北接吐谷浑,即指当时吐谷浑王城所在的赐支河曲,亦即河南地,则白兰地居河曲的西南,显然可见。其时党项羌居地在白兰之北,东北接临洮、西平,则利模徒实即在党项境内。《新唐书·党项传》谓:(北)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南界春(舂)桑、迷桑,北界吐谷浑。利模徒可能即为近白兰的党项别部,郍鄂也似为小部落,当在迷桑、嘉良之南。颉刚先生定其地位于附国东北,其说可从。杜佑《通典》说:“白兰,羌之别种,周时兴焉。”按宇文泰于(西)魏大统十五年(公元 550 年 )讨宕昌,白兰即于周武帝保定元年遣使献犀甲铁铠,而至保定四年(公元 564 年 )周遂灭宕昌置宕州,白兰盖于此时始见于记载。另外《周书》等都说其风俗物产与宕昌同,而宕昌正居同和郡 (今岷县)、武都郡(今武都)之间,当白兰之东,西倾山之西。如此则颉刚先生所考,确然不移。
其次,吐谷浑王视连居河南时,西秦乞伏乾归封他为白兰王;后又封视罴为沙州牧、白兰王,盖欲断吐谷浑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故为视罴所不受。西秦用武力进攻,他才退保白兰,说明白兰在河南地之南。
再次,吐谷浑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体,便呼其子叶延给大将纥拔埿说:
吾气绝,棺敛讫,便速去保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控。(《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 )
由于白兰地当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南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北控积石山,南依巴颜喀拉山,西北拒黄河天险,确是退保的战略要地。因此视罴、树洛干、拾寅等,都在受攻击时退保白兰。后魏时慕利延败走白兰,后魏军穷追,慕利延乃越巴颜喀拉山西奔于阗,在今南疆又开疆拓土,且略地远至罽宾。若以吐谷浑及白兰地在今柴达木盆地中部,则荒漠沮洳,非举族西迁所可能办到的。待后魏军撤退,慕利延又重返故土。
王忠先生据《新唐书·党项传》附白兰羌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敢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的记载,以为“白兰羌在党项之右,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有白兰,白兰羌当即自川西迁入青海,有人疑即因居巴颜喀拉山而得名,恐非事实”(见所著《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按白兰羌居党项之右,乃唐吐蕃时事,自西晋迄隋,党项实居白兰之北,约当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唐时多弥、松波(苏毗 )居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通天河流域,均在白兰西南。汶山郡距白兰所在地颇远,但西去即可与之相连属。至于是否即由此西迁(或东迁),则尚非片言所可断定。白兰部族颇大,在吐谷浑亡国后,他尚有胜兵万人,恐非原汶山郡小部所能组成。仅以汶山郡曾有白兰(按常志作“白兰峒”)的记载即认为白兰羌当即自川西迁入青海,亦乏确证。且白兰羌因居白兰山而得名,这并非顾祖禹所悬猜。《隋书·吐谷浑传》云:
吐谷浑与若洛廆不协,遂西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
其境内有白兰山,本无可疑也。《宋书》说白兰土出黄金铜铁,《新唐书》说白兰羌善作兵。善作兵是由于其地产铜铁矿,而地多黄金,则至今犹然,这也非柴达木盆地中、西部所可比。因此我仍认为颉刚先生《史林杂识·白兰》附图,定其地于果洛州部果洛山之西、巴颜喀拉山之东南端,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考定其地于今果洛州甘德、达日地带,当亦据此。( 关于白兰,其后我有《白兰国址再考》一文)
2. 沙州:吐谷浑阿豺在宋少帝景平中被刘宋封为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慕容璝于宋文帝元嘉九年也被授予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的头衔;西秦亦封视罴为沙州牧。这个沙州,显然不是指前凉所置在今敦煌的沙州。那么其地究竟何指?迄无明文。按《魏书·吐谷浑传》云:
阿豺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迥数百里,不生草木,因号沙州。
这里说这个荒沙滩,周回有数百里。前引《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则具体说:
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
是知沙滩地在吐谷浑王都之西,东西狭而南北阔。上文既已确定吐谷浑中期都城所在地在赐支河曲的河南地,则其西即为今海南州贵南县地。从贵南县去今同德县属的拉加寺,在其东南境有黄沙,其北部今名穆格滩(藏语穆格塘),而南部尤阔,其间不生草木,亦无人烟。我的妹妹昔曾经其地,据说单马清晨自沙滩北头向西南行,至晚始达南端的茫拉沟,足有一百三四十里。其黄沙中心正在茫拉,北逾黄河与共和县境的塔拉联为一片,面积更阔。颉刚先生近又在所著《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中引段国《沙州记》云:
浇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之若人委耩糠于地,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通鉴·晋纪》三十六,胡三省注引段国说,吴士鉴《晋书斠注》以为《沙州记》文,今从之 )读此,知道乞伏乾归任视罴为沙州牧,原来是这里的沙州,这沙州因这片黄沙地得名。那时西秦设立的沙州辖有西平、湟河、三河三郡,都在今青海省东部,也即吐谷浑疆域。(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顾先生据《沙州记》(按此文又见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条引)第一个明确指出了西秦所设立沙州的所在,才启示我得以进一步指出该沙州的今地来。何以说沙州故地即是今贵南县穆格滩呢?上引《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有云:
白兰土出黄金铜铁。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州。
慕贺州不见于地志,而其地在两晋南北朝时称莫贺川,或以为“州”即为“川”之误,我则以为西平、湟河、三河三郡既均隶沙州,而《宋书》谓其国大抵治慕贺州,则沙州应为汉名,而慕贺为其本名,实当为一地,慕贺、莫贺、穆格乃一音之转。穆格为今藏语,据温存智教授说,是饥馑、荒凉之意,我想引申可为荒漠,这与“荡然黄沙”“不生草木”相应。“慕贺”“莫贺”则当是吐谷浑原语,今藏语即其译音。与“慕贺”“莫贺”相近的译音,还有一个莫何川。《晋书·吐谷浑传》云:
(树)洛干十岁,便自称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号为戊寅可汗、沙漒杂种,莫不归附。
树洛干父视罴为西秦所败,退保白兰。其后视罴死,树洛干奔回莫何川,是其故地可知。“莫何”当为“慕贺”“莫贺”的同音异译。当时汉族对边地山川,译名多不一致,如沙漒以“羌”为“漒”,而在别处又仍用羌名,即是其例。《南齐书·河南氐羌传》又以慕贺川为幕驾川,“驾”为“贺”之误写,亦极显然。今柴达木盆地亦尚有莫何川,而共和县切吉,又或称莫合,都是一名的异写。两晋南北朝时的莫贺川,即为今之茫拉川,茫拉之名始于明代,为藏语的译音。
又,《新唐书,吐蕃传》云:
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踰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
此沙碛在且末、鄯善以西,原为吐谷浑西部,沙碛名莫贺延,正与莫贺川同。今蒙古语称沙漠亦为莫贺,吐谷浑原为鲜卑部族,其语言当与蒙古语同出一源。又《新唐书·吐蕃传》记刘元鼎使吐蕃所见有云:
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谷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在剑南直西。
刘元鼎把河南吐谷浑沙州境内的沙碛,也叫作莫贺延碛尾,则莫贺语义本为荒沙,得此证而益信。今藏语穆格义亦为荒沙,足证吐谷浑慕贺州所在即在今贵南县境内的沙漠内。今穆格滩有故城遗迹,俗称穆桂英城,传谓穆桂英西征至此,实则为穆格的音讹。设能对此故迹进行发掘,当可有所发现。
3. 伏罗川:刘宋元嘉十九年(公元 452 年 ),吐谷浑王拾寅始居伏罗川,近人或以伏罗川在今都兰县西部巴隆一带,我曾先后约加探索,但迄未能确指。今按《北史·吐谷浑传》云:
(魏)太武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
此处“河西”当作“阿曲”,盖形近而讠为。《北史·晋王伏罗传》云:
晋王伏罗,真君三年封,加车骑大将军。后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军至乐都,谓诸将曰:若从正道,恐军声先振,必当远遁,潜军出其非意,此邓艾禽蜀之计也。诸将咸难之。伏罗曰:夫将军制胜,万里择利,专之可也。遂间道行。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万部落。
《魏书·吐谷浑传》“阿曲”亦作“河西”。又,《魏书·晋王伏罗传》:
遂间道行,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阿曲。斩首五千余级,降其一万余落。
“河西”上二书均作阿曲。今兴海县大河坝原为阿木曲乎(或译阿粗乎)族住牧地区,为环海八族之一,当即阿曲旧地。大母桥当为赤水上的桥,即今共和县曲沟水入河处,在恰卜恰东南,居赐支河曲西端。在晋时前凉、前秦、南凉及南北朝时北魏均名其地为赤水,西魏始改称树敦城。隋移赤水镇于今兴海县,于其地置河源郡;唐于树敦城置金天军,亦即兴济梁所在。“大母”当为当地土语,或即吐谷浑语。伏罗此次行军,盖不取道浇河郡,而经由临津渡河至乐都,踰赤岭直捣赤水,慕利延猝不及防,惊奔白兰,而拾寅则退走阿曲,两人均系南奔。其部众作战地则在曼头城。《北史·太武帝纪》云:
(太平真君六年秋八月)壬寅,征西大将军、高凉王 等讨吐谷浑慕利延。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度流沙,
等讨吐谷浑慕利延。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度流沙, 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军拒战,
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军拒战, 击破之。中山公杜丰追度三危,至雪山,禽被囊及慕利延元子什归、炽盘子成龙,送于京师。
击破之。中山公杜丰追度三危,至雪山,禽被囊及慕利延元子什归、炽盘子成龙,送于京师。
前所云“伏罗遣将追之”,即指此。此所谓西渡流沙,即指由白兰奔于阗。至所云三危、雪山,盖泛指昆仑。伏罗川不在今柴达木盆地,即此可证。那么,伏罗川究何所指?根据此次战事在曼头城进行的事实,则其地实即曼头山(今共和县南山 )之阳,也即是今恰卜恰、曲沟(赤水)与曼头城(隋时远化县治)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从地图上看,这里正当唐代大非川的东南端,但当时既无大非川名,亦无伏罗川之称。伏罗川盖即因晋王伏罗出征至此而得名。伏罗此次出征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公元 445 年 )十月,慕利延走白兰;次年秋八月高凉王 率兵再追,慕利延走于阗。过了七年,到正平二年(公元 452年 )慕利延才又回故地。这年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于是汉文史籍上才有“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的记载,以出征大将名其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或许由于这并非吐谷浑本名,所以到隋唐时,又被改称大非川。“大非”可能仍是吐谷浑语,其义不详。
率兵再追,慕利延走于阗。过了七年,到正平二年(公元 452年 )慕利延才又回故地。这年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于是汉文史籍上才有“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的记载,以出征大将名其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或许由于这并非吐谷浑本名,所以到隋唐时,又被改称大非川。“大非”可能仍是吐谷浑语,其义不详。
4. 赤水:《南齐书》说吐谷浑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其中赤水到西魏时被改称为树敦城,北周因之,说已详前。这里主要考察一下它作为王都的情况。《周书·史宁传》云:
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将袭吐浑,太祖令宁率骑随之。军至番禾,吐浑已觉,奔于南山。木汗将分兵追之,令俱会于青海。宁谓木汗曰: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余种自然离散,此上策也。木汗从之。即分为两军:木汗从北道向贺真,宁趋树敦。浑娑周国王率众逆战,宁击斩之。踰山履险,遂至树敦。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浑主先已奔贺真,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兵攻之,退,浑人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奋击,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周回五十余里,欲塞宁路,宁攻其栅,破之。俘斩万计,获杂畜数万头。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宁还军于青海,与木汗会。
这是魏恭帝三年 (公元 556 年 )的事,上距拾寅始邑伏罗川,共 103 年,由赤水改称的树敦城,始终是吐谷浑王城,珍宝山积。史书上说吐谷浑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唯其北境多寒,仅得芜菁、大麦。赤水地处南境,气候较暖,水草鲜美,更宜养畜,所以富庶如此。在拾寅为王的几十年中,由于他屡通刘宋,接受封号,魏兵多次征讨,并入其境,刍其秋稼。这种既牧且农的地理环境,也可证明伏罗川并不在柴达木盆地。我过去推断伏罗川在今果洛境内,也是错误的。至于赤水镇(即隋河源郡所在)移设于今兴海,则是隋时才开始的,大概由于北周时史宁等攻破树敦城,城遭到破坏,不复成为军事要塞的缘故。另外,与树敦同时提到的还有个贺真城,这个城在史书上仅此一见,但它在当时却是与树敦王都并称的一大名城,乃是其新都。它的具体所在,当从以下两方面来加以考察
(1) 当魏兵在凉州集结时,吐谷浑王已奔南山,而仅留兵拒守。随后又说他奔贺真,于是木汗从北道趋贺真,而史宁从南道趋树敦,两军期会于青海,因此必须先求出南山的所在。此外所指南山,当是青海南山,它西北起今天峻县境内,东南迄于今共和县东北部,其东端正是树敦城所在地。这在唐代被称为大非岭,居大非川之北。吐谷浑王这次不南奔白兰,以避魏兵之锋,却出西北奔南山,则贺真城的所在,必须从这个方向去探索。
(2) 突厥木汗可汗是由北道进攻吐谷浑的,假设南道由浇河郡西行迳趋树敦,则北道必是越赤岭西趋南山。而吐谷浑后期王都,即在今青海西的伏俟城,贺真城当是伏俟城的早期名称或即在其附近。这时正值夸吕在位,史载伏连筹死后,夸吕即移都于伏俟城,在这次战役开始前,他已先奔贺真,最后贺真终被木汗攻破,并掳其妻子,按理伏俟城即在南山北端,却并未再提到。如此则贺真实即伏俟城,可能夸吕初移都时,该城尚名贺真,经此次战役后,始定名为伏俟,而大多汉文记载,统以伏俟概之,因此贺真一名,仅见于《史宁传》。否则木汗在破贺真后,便不会弃伏俟城王都不攻,而迳回军与南路来的史宁会于青海了。
史载伏俟城距青海十五里,其遗址近在共和县东北角上的石乃亥发现,城内有王宫等遗迹,与史载有城郭而不居的说法相吻合。当时对吐谷浑的城池称为大戍,似主要只起军事堡垒作用。
以上从南山方位的推定及南北两军会师于青海的实况,得出贺真城即伏俟城的结论,似可供历史地理学者们作进一步探讨。
伏俟城在隋于大业五年灭吐谷浑后,就其地置西海郡。隋末大乱,吐谷浑王伏允又复返故地,至公元 670 年,伏允走西平附唐,吐谷浑东部王都伏俟城,遂没于吐蕃。
5. 屈真川:吐谷浑四大戍之一的屈真川,或称吐屈真川,吐当为吐谷浑的省称。我原推测它或即是伏罗川的原名,兹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有云:
屈真川有盐池,甘谷岭北有雀鼠同穴。
在吐谷浑境内,盐池所在多有,但此当指较大者而言。今海晏县(王莽时置西海郡 )近青海湖边有碱池,在地理上偏于东北;又一即茶卡盐池,在地理上居于伏俟城西南端,《宋书》所指,可能即此。中原王朝对吐谷浑用兵,向未到过此地,所以史书上迄未再提到过。若此项推断可以成立,则屈真川即为今茶卡滩。古时以山区平原为川,如秦川、勇士川、苑川、捏工川、茫拉川,均是其例。后世或称原,如长武原、董志原是。茶卡滩今为放牧骆驼之地,鲜有人居住。吐谷浑当时也养驼,魏废帝二年,史宁曾截获其通齐使者,并驼骡六百头,杂綵丝绢以万计。盖骆驼是当时运输工具,特别是远徙且末、于阗,更非此“沙漠之舟”不行。又,骆驼喜食碱蓬,此草唯盐碱滩才能生长。甘谷岭当指由茶卡北去天峻的山脉,日月山西北与西南地区,均有雀鼠同穴,唯柴达木则鲜见。
6. 清水川:清水川亦为吐谷浑大戍之一,且序列于首。我原以为它在洮水流域。今夏得梁今知先生书,谓日人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认为清水川即今之循化县清水河。按此所谓清水河在今循化县城东十余里处,北流注于河,源于其南大日加山,北流贯行道帏沟,至清水庄注入河,并无所谓川原,容当别求之。
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条在叙及吐谷浑造黄河桥“河厉”时,引段国《沙州记》后说:“桥在清水川东也。”佐藤长即据此定其桥当在今循化城东,而河于此处穿行小积石山峻谷中,无径可通,直至临津废城(今临夏大河家地),河始出峡,为向来津渡处,至今仍用舟摆渡,迄无津梁记载。即使间或造桥,亦只能造舟为梁,即后世所谓浮桥,而“河厉”则为握桥,不宜建在河水平缓之处。因此,我颇设想此桥当在赐支河曲峡谷中,清水川在浇河郡(今贵德县)迤西共和县境内,因为,当时吐谷浑王都即在沙州地区,宜有设防建置,以拱卫首都。当时记载吐谷浑大戍的序列,首清水川,次赤水,次浇河,此二戍均在赐支河曲,清水川当去此不远(今共和县境内,藏名亦有清水河,与黑水相对而言 ),只是由于记载阙略,无从旁证,所以仅对其地望作如上推测,尚不能确指其所在。不过,它非指今循化清水,则可断言。至于洮水流域大戍,则应以洮阳、洪和二城为最著,不当更以今清水张家川地区为戍了。
7. 阿柴:《晋书·吐谷浑传》云:
(吐谷浑)地宜大麦而多蔓菁……西北杂种谓之为阿柴虏,或号为野虏焉。
(树)洛干十岁,便自称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漒杂种,莫不归附。
吐谷浑自叶延起,便以其祖名吐谷浑为氏。而到了沙漒杂种归附树洛干后,他们又把吐谷浑称为阿柴虏。这个名称,当由树洛干弟阿豺立为吐谷浑王后产生的。“柴”“豺”音同,便以首领之名称其族。后来吐蕃兴起后,也称吐谷浑族为阿辖,“柴”“辖”古音同部,“辖”字是我所译音,据此“柴”当读如“辖”音。《文献通考》作“阿赀”,赀,即移反,亦与“辖”音近。(说别详)
阿柴虏或阿赀虏既系指树洛干以后的吐谷浑族,则其中心地当在沙州与漒川之间。漒即漒台山,川即洮水。《水经注》卷一河水有云:
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嵹台山,山南即垫江源,山东则洮水源。《山海经》曰:白水出蜀。郭景纯注云:从临洮之西倾山东南流,入汉而至垫江,故段国以为垫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嵹台西倾之异名也。洮水东北流迳吐谷浑中。
阿豺时吐谷浑势力中心既在沙州与漒川地带,则目前中国历史地图,均把阿柴居地划在今柴达木盆地中西部,殊与史实不合,应行改正。至于唐以来吐蕃文书等所称的阿辖或霍尔 (即浑的音转),则更遍及于今青海省北、东、南三部并四川甘孜等地区,这虽是后来演变情况,但迄无指今柴达木地区者。然则后来把阿柴居住地区集中在今柴达木盆地,与事实就更相远了。
吐谷浑历史地理的可考者,略如上述。其中有些辄未敢与时贤相从同,此并非有意立异,姑自别为一说,聊供大雅审订云。
( 三)吐谷浑“河厉”
吐谷浑居河南时,曾在黄河上游建桥,名曰“河厉”。“厉”当取《诗经》“深则厉,浅则揭”之意。《水经注》卷一河水引段国《沙州记》云:
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
按这种桥的建造形式,是握桥型。想来段国当时是曾看见过这座古代桥梁的,所以讲得很细致。握桥因无桥墩,所以只宜建在水面狭窄的峡谷间。两岸就原来石基,用大木纵列叠加横梁为础,逐层延伸入河中,直到相距三丈至五丈多宽时,则更用巨梁十余根,纵贯两端,上铺木板,并在两边加上栏杆,人马即可通行无阻。此种桥型,过去在黄河上曾在化隆与循化之间的古什郡峡中先后建造过两次;另外西宁小峡湟水及享堂峡大通河上所使用的也是这种桥。小河流沙而不易立墩下桩的也间造握桥,可谓源远流长。握桥的名称,当由“幄”“楃”引申而来,幄为布帐,楃为木帐。旧时兰州雷坛河因常发洪暴,也建有握桥,上有木棚如屋,即是其证。
吐谷浑所建的这个握桥,究竟在何处呢?就段国在记述沙州时提到此桥,而郦道元也在为沙州作注时引段国说两事来看,此桥当在浇河郡以西沙州境内。今考汉时贯友为护羌校尉,攻迷唐,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于河峡作桥渡兵,迷唐遂远依河曲。钟存羌部居地在西倾山西北(今青海泽库及河南县地区 ),迷唐原居大、小榆谷(今贵德、尖扎地区)以为汉造河桥,兵来无时,不敢返回。这座桥是浮桥(作大船),在建威城所在,即今贵德、尖扎两县之间。贵德在解放前也还有浮桥。吐谷浑王都时在沙州,而且是握桥,自不会建在这段河上。唐时在九曲先后建立金天军、九曲军和独山军,金天军在今共和县,九曲军在今贵南县,独山军在今同德县,都在河曲内。后曾在金天军树敦城造洪济梁,其地正当吐谷浑时代的赤水。此或即吐谷浑桥的旧址,当沙州之北,浇河郡之西。
其次,北魏于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 460 年 )征吐谷浑时,曾渡河追击拾寅。《魏书·高宗纪》云:
八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什(按即拾)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获畜二十余万。
这次出军,是采纳了定阳侯曹安的建议,他说:
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相近,明其意势。若分军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月,牛马草尽,人无所食,众必溃叛,可一举而定也。
于是命阳平王新成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出北道以讨之,拾寅果走南山,诸军渡河追击。按此南山即前所述青海南山,出浇河的南道军必须渡河追击,而当时河曲正值秋涨季节,且无河水,必须取道河桥,如此则此桥必在赤水一带。设当时河曲无桥可跨,则南军势不能与北军会攻南山,这也是可断言的。果如佐藤长所考“河厉”在循化县境,则更无所谓“济河追之”了。
史称吐谷浑族善作兵,而且由于它吸收了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并擅营造,如梁时在今成都建造佛塔和这座握桥工程,这在文化史上都是值得称颂的。
摘自《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
热门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