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碉楼海棠花 : 藏地班玛纪行
2019-01-10原文地址
寻找一棵树
文/古岳
两个月之后,我专程到玛可河谷的班前村去寻找这棵桃树。
我也确实找到了一棵树,确切地说,是找到了两棵树,但那都不是桃树。我所找到的那两棵树,一棵是杏树,另一棵是柏树。不过,在见到那棵杏树之前,我却曾以为自己找到了那棵桃树,因为,当我向村里人打听那里有没有一棵桃树时,他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大喜过望,急匆匆赶去探望。可是,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所看到的却是一棵杏树。
我熟悉桃树,更熟悉杏树,自己还种过很多杏树。我所种下的杏树少说也有上百棵,我不会分辨不清哪棵是桃树,哪棵是杏树。因为时至初秋,在树下,我还捡到了一个熟透了自己落下来的杏子。但是,班前村的人却不叫它杏树,而是叫桃树,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棵桃树。进一步地调查核实中我得知,迄今为止,这棵杏树是整个班玛县唯一的杏树。因为以前当地既没有桃树也没有杏树,当地人没见过桃子也没见过杏子,难以分别桃杏。后来,有了这棵杏树,见了杏子,便误以为它就是桃树。
那棵杏树也并不在一个小院里,而是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原本是一棵树,因为树干从树根里就开始分出枝杈,长成了五六根树干,除中间三四枝一直在向上生长以外,旁边两根竟歪歪斜斜地向两边伸展出去,几乎是横着生长的。其中一根旁枝毫无顾忌地伸向这户人家的门厅,出入时有所妨碍。
据说,这家主人曾一度很想把那一根斜枝砍了,却并未擅自行事,而是找到一位有声望的活佛,小心询问,是否可以砍了那根斜枝。活佛回答说,他知道那棵杏树,非但不能砍了那根斜枝,还得细心呵护,非但那根斜枝不能砍,那树上的一枝一叶都是不能动的。至于为什么不能砍,活佛没说,他们也没敢问。于是,那棵杏树长得更加随性自在了。
难道有关那棵桃树的传说是某个人一厢情愿的讹传?我有点不甘心,也不死心。我给在班前村乃至玛可河谷所见到的每一个人一次次讲述那个传说,希望有人能记起那个传说,想起记忆深处的那棵桃树。可是,没人知道那个传说。
于是,又向每一个人说起那两只太阳鸟,我说,每年桃花开时那两只太阳鸟就会飞来,落在这棵桃树上,花谢了才飞走。有关这两只鸟,他们的回答都非常肯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见过这两只鸟。他们说,那两只鸟飞来时,就落在那棵他们视为桃树的杏树上的,雅格多杰也是在这棵树上拍到那两只鸟儿的。
但是,那棵桃树却一直无踪无影。
有一天,一个叫益西贝太的人告诉我,十世噶玛巴与七世红帽噶玛巴确实在这里种下了一棵树,而且那棵树还在。不过,那并不是桃树,而是一棵柏树。他是七世红帽噶玛巴的后裔和族人,他的讲述像黑暗中点亮的一盏灯,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虽然,这是一棵柏树,但它至少说明这两位大师在这个地方是种过树的。既然,他们能种下一棵柏树,说不定也能种下一棵桃树的。
十世噶玛巴一生游历,别说是桃树,他应该是什么树都见过的。而且,根据他在佛学、绘画等诸多领域的高超造诣,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会细心留意,更不会轻易错过欣赏一树桃花的机会。这样一个人从远方带来一粒桃树种子,种在他决意抵达的那个地方,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寻找这棵桃树。益西贝太说,他有一个弟弟是吉德寺活佛,很有学问,说不定会知道这些事,便领我去拜访。
吉德寺就在班前村后面的山坡上,相传,第十世噶玛巴到这里见到第七世红帽噶玛巴之后,并不想很快离开这里。不仅因为年幼的七世红帽噶玛巴需要他的陪伴,这里也是他自己的出生地,他想多住些日子,亦可慰思乡之情。益希宁宝觉得这是件大事,不能马虎,他不能让至高无上的噶玛巴随便住在一个地方。他决定专为噶玛巴建一个驻锡地。十世噶玛巴住过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成了一座寺院,这个寺院就是吉德寺。
在吉德寺,噶玛旦巴活佛热情地接待了我。当他得知,我专为寻找一棵桃树而来时,他多少有些惊讶,但还是耐心地跟我进行了交谈。他说,他也没有听说过十世噶玛巴曾在这里种下过一棵桃树的事。我注意到,在提到那棵杏树时,他也说那是一棵桃树,只是指出,那棵“桃树”并非噶玛巴所种,而是一个叫尕藏的人的父亲所种。尕藏的父亲小时候也曾在吉德寺出家为僧,后来还俗当了国家干部,还当过班玛县的人事局局长。他从小聪慧过人,兴趣广泛,不仅博览群书,大有学问,而且写得一手好字,1949 年后班玛县很多单位门前牌子上的藏文名称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年轻时,一次去四川藏区,带回来一棵不小的树苗,种在自家门口,说那是桃树,从此人们都叫它桃树。
那些天,我多次到这棵杏树前,上下左右仔细打量。它枝叶繁茂,主干胸径至少在50 厘米以上。这个地方的海拔不算太高,但也已超过了3600 米,对一棵杏树来说,这也许是它能存活的极限高度,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杏树是一种生长速度极为缓慢的落叶乔木,即使在低海拔地方,长成这个样子也需要四五十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在班前这样的高寒地区,一棵杏树要长成这个样子,至少可能需要七八十年的时间。很显然,它所经历的岁月,在一个人看来已经足够漫长,称得上是一棵老树了。当年种它的那个年轻人早已不在人世,它却依然充满活力,根深叶茂。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不测,再过七八十年,它说不定会依然在那山坡上婆娑婀娜,甚至可能更加葳蕤壮观。
可是,我苦苦寻找的并不是一棵后世所栽种的杏树,而是一棵栽种于350 多年前的桃树。按理来说,一棵杏树要活到350 多岁,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一棵桃树绝不可能活那么长久。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劫数和定数,难以逾越。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当年十世噶玛巴所种下的就是一棵杏树,因当地人桃杏不分,而误认为那是一棵桃树呢?如是,那棵杏树而今安在?当地缘何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棵“桃树”的蛛丝马迹呢?这也是一个疑问。令我疑惑的还有,如果这样一棵桃树或杏树真的存在过,那么,它曾长在什么地方?
传说,它就长在七世红帽噶玛巴出生的那个院落,可而今那个地方,曾经的那个院落早已不再——虽然,现在那里也有一个临时围圈的院子。那个地方,现在有一座白塔和一尊汉白玉雕像,白塔是七世红帽噶玛巴的纪念塔,雕像是七世红帽噶玛巴的纪念像。我曾多次走进那个院子,去追寻和怀想。除了白塔和雕像,我只看到了荒草,别无他物。按顺时针方向绕着那白塔和雕像走去时,我的步伐非常缓慢,而且,每迈出一步,都十分谨慎小心,生怕不经意间会踩到圣迹。可我没看到任何与一棵桃树或杏树有关的迹象。
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便当年噶玛巴种下的也是一棵杏树,而非一棵桃树,它也早已不复存在,成为虚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棵杏树绝不是当年的那棵杏树。那么,传说中,那棵一次次死而复生的桃树呢?它而今安在?难道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又或者,即使存在过,也早已幻灭。在佛家眼里,即使眼见的一切存在,包括大千世界,也是一种虚无,并非真的存在,何况草木。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那个传说是否是一种有意为之?其本意也许并非要让人去寻找这棵桃树,而是要让人去探究事物的本源。要是这样,我其实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苦苦寻觅一棵并不存在的桃树,这无异于用实证的方法求证一道深奥的哲学命题,终归是要无功而返的。可是,我并不认为自己一无所获。我所收获的也许只是这样一次不寻常的寻访经历,也许还有寻访途中的所思所想,也许还有别的,至于那会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找不到那棵桃树,我又开始寻找那棵柏树。
噶玛旦巴活佛也提到了那棵柏树。他虽然不能确定那是不是十世噶玛巴亲手所种,但他肯定这棵柏树确实与十世噶玛巴有关,也与七世红帽噶玛巴益希宁宝有关,说不定是他们两个人一起种下的。他还说,原来那柏树跟前有一块巨石,七世红帽噶玛巴幼年骑马出行时,常常踩着那巨石跨上马背的。
我找到了那棵柏树,它就在班前村头的玛可河边上。河上有一座早已废弃不用的吊桥,那棵柏树就长在离河右岸桥头很近的地方。很久以前,这里也有一座桥,但不是吊桥,而是一座木桥。
传说,那木桥也是十世噶玛巴与七世红帽噶玛巴一起修建的。在为这座木桥选址时,十世噶玛巴下到河边蹲在一块礁石上,脱下一只靴子说,他要把靴子扔进河水里,让它往下淌,到了一个地方,它会停下来,在河水中不停地旋转,那个地方就是造桥的好地方。那靴子在河水中淌了不远果然停下了,还在河中央的一个地方不停地旋转起来。十世噶玛巴就挑选了一根粗壮的木头,让人们把那根木头立到靴子转圈的那个地方。木头放下去之后,竟牢牢地站住了。原来,靴子旋转的地方有一个漩涡,漩涡底下河床有一块巨石,经河水千万年冲刷,形成了一个垂直向上的窟窿,那根木头放下去之后,就像一个楔子楔入开凿好的卯孔里,像古建筑中的榫卯结构,恰如其分,坚固牢靠。以此为固定轴心,用捆绑木头和用石头垒砌加固的方式,一个桥墩就立起来了,一座木桥就这样建成了。
直到20 世纪中叶,那木桥尚在使用。后来,才改建了一座吊桥。再后来,上游不远处又用钢筋水泥建了一座更加结实的新桥,那吊桥也废弃了。那种木结构的桥梁,在西藏昌都附近的澜沧江流域河段,至今还能看到。它是智慧和慈悲的造化。
在那棵柏树前,我没看到七世红帽噶玛巴益希宁宝骑马时踩踏过的那块石头。柏树下,我所看到的石头都是刻有经文或六字真言的石头,那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几百年来人们不灭的信念和善愿。藏区到处都有这样的石经墙、石经堆,有些石经墙、石经堆堆砌到了令人震撼惊叹的地步。像玉树的嘉纳嘛呢石堆,由几十亿块刻着经文、佛像和慈悲咒语的石头堆在一起,那已经不是一个石堆了,而是一个石城,所以,人们就叫它嘉纳嘛呢城。班玛以前也有一座这样的嘛呢石城,就在离此地不远的玛可河上游谷地,那个地方叫江日堂。
据说,那个地方嘛呢石堆曾经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嘉纳嘛呢。20 世纪60 年代后被毁,近几十年虽然有所恢复,但要恢复到昔日的壮观景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很多流离失所的经石又回到了曾经摆放供奉的地方,但是,更多的经石早已不知所踪。这些年又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刻了很多新的经石,不断堆砌、摆放和供奉,以期重现往昔的辉煌和灿烂,也许过不了多久,蔚为壮观的江日堂嘛呢石城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仔细留意过那棵柏树下的经石,那都是一些并不厚实的石板。与其他藏区很多地方所见到的经石有所不同的是,这里一些石板上虽然也刻有六字真言,刻有佛像,但绝大部分石板上刻着的是整段整部的经文,都用藏文字雕刻而成。大多石板上的经文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不少石板上的经文已经出现脱落,石板表面斑驳,侵蚀痕迹明显。
那石堆旁,沿河有一条水泥路通往村庄。益西贝太说,修这条路时,还从路边山坡上挖出了很多刻有经文的石头。那山坡上建有一个塔状的祭台,是十世噶玛巴和七世红帽噶玛巴特意为供奉一处泉眼而修建的。泉眼原本就在河边上,因为恰逢雨季,河水上涨,泉眼已经完全被河水淹没,看不出它的样子。挖出来的那些经石没地方摆放,只好与柏树底下的那些经石堆放在一起。这些经石紧挨着那柏树的根部围城一圈,码放着,形成了一个高一米以上、厚度也接近一米的圆形高台。因为石堆长期堆放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石之间的缝隙早已被尘土填满,历经风雨,石堆上长满了青苔和杂草,严严实实地包裹着那柏树的根部。
那棵柏树的树干从根部开始就分成了三根,要是不知道它的历史,一眼看过去,你会认为那不是一棵柏树,而是三棵柏树。这是一棵十分高大的柏树,树高十余米,树干胸径在70 厘米左右。在这
样的海拔高度,一棵当地柏树至少要长三五百年以上才能长成这个样子。单从树龄看,它真有可能是十世噶玛巴和七世红帽噶玛巴所种植。如是,这当是一棵世间所罕见的柏树,不是因为它的植物属性或科学价值,而是因为藏传佛教史上的两位传奇式伟大人物。一棵树,哪怕它是一棵柏树(或一棵杏树,或一棵桃树),说白了,它就是一种植物,竟有两位伟大人物精心栽培,这是何等样的造化和福报!
可惜的是,其中的一根树干已经枯死。我确定,这与它根部的石堆有关。因为有一米多高的一个石台密实地围裹,不透气,也没有足够的水分。这相当于把柏树的根拔出了地面,且离地面已经有一米多高了。长此以往,那树必死无疑。在藏区行走时,我留意过,此类现象非常普遍。
整体而言,藏人自古崇拜大自然,信奉众生平等,对神山圣水的祭拜从未间断过,这是藏民族传统生态理念或习俗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它不变的主题。可以肯定地说,整个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之所以得以很好的保护和延续,文化基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如何解决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全球性课题,藏文化对大自然卓越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启示显得尤为珍贵。
但是,班前村那棵柏树已经干死的那根树干并非特例,类似的现象在藏区亦可谓普遍。一些寺院或村庄附近,或一些神山圣水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棵树下,刻着经文、真言和咒语的石头垒了一圈又一圈,其中的有些树已经干死,还有一些树也正在枯萎。不仅是嘛呢石堆,还有那些在山冈上飘荡的经幡。有些地方,千百年下来,经幡挂满了山野,一层层不断叠加,把整个山冈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如果山上原本有树,它们就在树上缠绕,很多树就干死了。
站在那棵柏树下,望着它已经枯干的那根树干,我对益西贝太说,如果不尽快采取果断措施救救这棵柏树,过不了多久,另外的两根树干也会干枯的。建议他跟村里人商量后,把树根里的经石取出来,重新摆放,至少要把挨着树根的那些经石挖出来,摆放到离树根远一点的地方,可以摆放得更加整齐,但一定得离开树根。这样树才能充分吸收养分,才能活下去。他说,面对这些经石,村上的人只会磕头跪拜,没人敢动这些经石。
为此,在拜访吉德寺噶玛旦巴活佛时,我特意提出一个请求,请他跟吉德寺其他高僧一起主持举行一个仪式,搬开柏树根里的那些经石,救救那棵柏树。噶玛旦巴活佛爽快地答应了。已经枯干的那根树干可能再也无法重新长出枝叶了,但是,还没有死去的那两根树干因此应该能继续生长。
因为我的缘故,能救活一棵树是莫大的安慰,能救活一棵已经长了几百年的柏树那更是奇缘。因为,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柏树,它是一代宗师第十世噶玛巴和第七世红帽噶玛巴共同种下的一棵柏树。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是一种植物,经历了人们数百年的敬仰之后,它应该已经长成了一种精神。千万不要把这样一种情怀简单归结于宗教,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该是一句空话。只有与一株青草、一棵树、一滴水、一朵花、一片云、一只鸟、一只爬虫、一片土地等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才会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有一天,我也许还会去看这棵树,或两棵树——一棵杏树,一棵柏树,但愿我去的时候,它们还在那里,枝叶繁茂。也许不会去了,如果是那样,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仍能听到它们的消息,希望它们自在安好。
摘自《雪山碉楼海棠花 : 藏地班玛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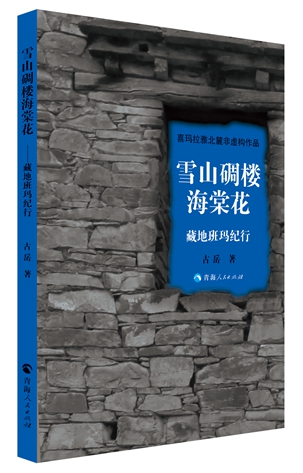
热门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