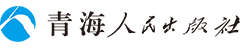森林的光芒
2019-08-08摘自《雪山碉楼海棠花:藏地班玛纪行》原文地址
森林的光芒
文/古岳
我曾说过,一棵云杉的样子就是慈悲的样子。
多柯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河谷两岸山野之上曾经都是森林,阴面山坡上几乎都是云杉。但是,那天当我再次走进这条河谷时,河对岸那整个一面山坡上的森林都已倒在山坡上。那面山坡长约30 公里,上面曾经都是茂密的川西云杉,直到1998 年时,它们还那么苍翠浓郁着。在那道禁伐令下达之后,竟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在几天之内就将那片森林统统伐倒在那里。此事惊动了共和国总理,他大怒,便又下了一道命令:即使让那山坡上已经砍伐倒地的林木全部腐烂在那森林里,也不准任何人往外运出一根木头。用心可谓苦矣!但是,不如此就不能禁绝砍伐之害。站在河边的滩地上,凝望着那些乱纷纷倒在山坡上的那一棵棵大树时,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尸横遍野的情景,它会使人想起诸如国殇之类的字眼。
有一幅画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已想不起画家的名字了——好像是吴冠中,但记得那是一幅国画,一幅具有油画般凝重效果的国画:黑暗的天空上,滚滚乌云严实地压向大地,像山一样四面环绕着,前面是平坦的原野,原野之上是无数战死沙场的烈士,一片死寂、一片宁静之中,有一匹白马像是在寻觅青草,又像是在用嘴唇轻轻触碰它的主人,无边的忧伤就在它的四周弥漫。画名就是《国殇》。站在多柯河谷地,凝望着那面躺满了林木的山坡时,我就仿佛站在了那幅《国殇》之前,那也是尸横遍野的沙场,那也是战死沙场的英烈。
多柯河阳坡多有圆柏分布,一路走去,林间密密麻麻的伐桩触目惊心。我曾仔细端详过一棵圆柏的伐桩,上面的年轮已经模糊,但它还完整地保留着油锯切割的截面。它的直径足有一米有余,想来它在这河谷山坡上已经挺立了2500 年以上。
多柯河已是长江流域了,与多柯河只有一山之隔的玛可河也是长江流域。与多柯河不同的是玛可河流域依然是一座大森林。从林间公路上穿林而过时,两旁的森林看不出曾经遭到过多大的破坏。林相还保持着原始的模样,林缘地带的植被还没有出现退化,林下灌草茂密,林间山沟之内清流潺潺,一派万物和谐、鸟语花香的景象。
我曾先后多次去玛可河林区,第一次是在30 年前的那个夏天,与其说我是去看那片森林的,倒不如说我是到那片森林里去找一个人的。但是,我没见到这个人,却因为穿越一片片森林去寻找,记住了一片森林,并被它深深吸引,以至不远千里一次次造访。我去专程寻访的这个人是我儿时的同伴,有一个夏天,我们在同一座山上放过羊。
那是1968 年的夏天,那一年我们都6 岁。因为那一年的一场冰雹将庄稼洗劫一空,很多人家都没有粮食吃饱肚子,我们两家也一样。其实,他们家并不在我们村上,也不在同一个公社——那时候今天叫乡镇的这个行政区划单位还叫人民公社。他一个姑姑在我们村上,因为膝下没有子女,吃饭的嘴少,日子相对好过一些,他就到姑姑家里帮着放羊,好混口饭吃。而我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姑姑,即便吃不上饭,也得留在自己家里忍煎熬。于是,我们就成了一同牧羊的伙伴。也许是因为苦难岁月的磨砺,尽管我们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太多过于亲昵的故事,但是很多年以后,等我们都长大成人了,那山坡上一同经历的点点滴滴却成了宝贵的铭刻,难以磨灭。于是想念,于是去寻找。
但是,那一次我走遍了整个森林也没见到他的面。刚刚听说他在一条山谷里伐木,急急赶去时,他却又到了另一条山谷……这个人就是赫万成,记得他当时是玛可河林场的采伐队长,后来当了玛可河林业局副局长、局长,直到离开玛可河到省林业厅任职,在那片森林里生活和工作了30 余年。直到1998 年夏天,我们才第一次相聚,相隔了整整30 年。见面的地点不在玛可河,而是在西宁。相见时刻,忆及当年,彼此都是满眼泪花。第二次去玛可河时,他已是副局长了,一到那里,就见到了。那一次,我在玛可河住了半个月,因为一项拍摄任务,整个林区几乎走遍。
第二次和第三次去玛可河已是十几年之后了——之后又去过很多次。我在玛可河的日子加起来差不多有两个月时间,用两个月的时间去认识一片森林不能算长,在我却已是很奢侈了。除了玛可河,我在一片森林里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星期,大多都在三两天时间。应该说,我已经了解了这片森林,也深深地感受过这片森林。玛可河林区是青海境内在长江上游最大的一片森林,属大渡河水源涵养林。玛可河及其支流每年向长江输送着超过16 亿立方米的清流碧浪。玛可河流域是青海诸河流域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好的地区之一,其森林覆盖率当在70% 以上——而青海很多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尚不足40%,还不及很多国家乃至国内一些地方国土总面积上的森林覆盖率高,要知道,那可是林区啊!
其实,玛可河林区也曾是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森林之一。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林区内的砍伐之声从未间断。像麦浪沟那样整条山谷全面采伐的地方也不止一处。直到1998 年底国家开始实行天然林全面禁伐之前,这里的可利用森林资源已濒临枯竭。这里分布着多达460 余种森林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森林中的看家乔木当数川西云杉,其次是桦树和松树类,而分布最广、种类最多的还是林下和林缘地带的灌丛。这些森林从海拔3500 米的河谷一直长到4000 米以上的高山之顶。因为地处高寒,一棵云杉小树苗要长到根径有碗口粗的样子需要120 年以上的时间。而在那些大肆砍伐的年月里,一个伐木工用油锯砍倒一棵有300 年树龄的云杉所用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一棵大树生长的历史是它被砍倒所需时间的3600 万倍。这一快一慢之间造成的就是神州大地上一串串永远无法改写的森林赤字。
这里几十年间采伐的林木从数字上看也并不很多,总计也就100 多万立方米,森林总消耗量也不过200 万立方米,加上盗伐和其他原因导致的损失,估计也不会超过300 万立方米。问题就出在林木生长速度的缓慢和砍倒一棵树所需时间之短暂之间所形成的落差悬殊。麦浪沟深约20 公里,两面山梁之间最宽七八公里,山架垂直高度在1000 米左右。偌大一条高山深谷之内曾经都是茫茫苍苍的林莽。20 世纪70 年代初至80 年代初,浩浩荡荡的采伐大军整整用了10 年时间,采伐这条山谷里的所有可用之材,总共才出过12万立方米的木材。依浪沟的森林也采伐了近10 年时间,但只出过六七万立方米的木材。由此可以想见,那300 万立方米的林木消耗量需要砍伐掉多大的一片森林。
第一次走进玛可河森林时,我感觉自己正走进一座庞大的木材加工厂,到处码放着山一样的原木,设在一些山沟里的木材加工点上,电锯的尖叫声从早到晚不曾间断。随那电锯的尖叫一棵棵高大的树木就变作了一块块木板、一堆堆锯末。每一面山坡上都躺满了被砍伐倒地的林木,每一片森林里都传来伐木的轰响。通往山外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林木而去的大卡车不堪重压吱嘎作响。而我所眼见的一切也许还不是最惨烈的场面。
1967 年至1970 年,玛可河的交通不畅,为运送木材,林场专门修了条公路通到四川阿坝,并在那里建了一个有80 辆大卡车的转运站。这个庞大的车队每天都从森林里把砍伐的木材运至阿坝。再从阿坝运至黄河加曲段的码头,再从那里直接往黄河里倾倒,让那些林木从黄河上游往下游漂浮。整整三年时间,加曲至曲沟近千公里的黄河上一直流淌着玛可河的原始森林。国家通讯社曾发电稿称赞这是世界高海拔地区最长的航运河道。
从1970 年开始,玛可河的林木直接运往四川,每立方米木材的售价只有50 元。而每运出一立方米的木材,林场还赔进去近10 元的血本。所以从1971年开始,玛可河开始自己加工木材,最多的一年就地加工的木材高达7 万立方米。一片森林就这么消失了,而带给玛可河伐木工的却是连年亏损的重负。直到1994 年以前,玛可河林场没有因为大量砍伐森林而取得任何经济效益,甚至已到了砍伐越多亏损也越严重的程度。后来,他们不得不自己经营木材,才使情况有所扭转。这已是1995 年的事了。
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德斯教授曾详细测算过一棵树的生态价值:一棵50 年树龄的树,产生氧气价值是31200 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的价值约62500 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 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 美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地价值31250 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 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创造价值196150 美元。
是的,这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以金钱来作衡量尺度的年代,可在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用什么来作衡量金钱的尺度。德斯教授的计算肯定是科学的,但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的苦心呢?依他的科学计算,我们从玛可河这样的森林中砍伐掉的那些高大的树木意味着什么呢?
我第二次去玛可河是在一个秋天。那里的砍伐之声已经消失,森林已恢复了宁静。秋色已把森林涂染得几乎到了金碧辉煌的程度,但只是渲染,不夸张,也不杂乱,有的只是和谐,只是色彩绚烂的统一。落叶松的针叶黄得像一片片金色的羽毛,透着亮、发着光。白桦的圆叶却是黄中带红,微风过处,它们在一面面山坡上如一群闪动着翅膀的蝴蝶。绿中透出瓦蓝色光芒的是云杉林巍然耸立的身影。林间流泻着一层层细碎金色波浪的是高山柳类尖尖的细叶儿。用深红和金黄涂满整个一座山梁升腾着五彩烈焰的是高山灌丛的景致。山间的清流碧浪一路流淌着森林斑斓的色彩,涓涓潺潺的流水声里尚能听见一声声鸟儿的啼啭脆鸣。有白云在林莽之上浩荡,有鹰自白云之下飞翔。山冈之上有土著藏族的碉楼山寨,山寨深巷之内有狗在吠叫。天地岁月情长,自然万物一脉。一片片秋色就是一段段金色的乐章。一棵棵大树就是一首首大自然的情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玛可河的秋天是岁月的诗。望着那一派美景,你就会自惭形秽,你就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天地间可以没有人类,但绝对不可以没有森林。
整整有半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那无边的秋色林莽中徜徉流连,每天都到那林间空地上独坐很长时间,坐在那里时,你即使闭目遐想,那滚滚而来的秋色也会随阵阵松涛穿透你所有的神经。面对那样一种至美的景色时,你即使是个龌龊猥琐之流,也会生出满脑子至纯至善的感念和祈愿。且不说,森林对人类生存的绝对意义,就是它对人类灵魂的净化乃至教化意义也是无可替代的。那是个雨后的下午,我在森林里漫步,草叶上、树叶上和松针上闪动着无数颗晶莹透亮的露珠。像无数颗玲珑的小铃铛,坠挂在一座巨大的绿色殿堂里。在绝对的宁静中,摇响着一支令人心魂飘荡的谣曲。
甘长富曾是一个伐木工,如今却已是森林护林队的负责人了。那天一大早,他就领我去看白马鸡,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翻了好几座山,穿过了一片又一片密林,却连一只白马鸡也没看到,只听到过几声马鸡的鸣叫。他觉得很奇怪,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4 年,当了20 年的伐木工,他见到过无数的白马鸡,在那些漫长的冬天里,他常常以打猎来作消遣。每年冬天,他猎获的蓝马鸡和白马鸡至少也在百只以上,当然,他猎获的不只是马鸡,还有石羊和别的动物。他自言自语:“怎么就一只也看不到了呢?”最终我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寻找白马鸡的努力,就坐在一道山梁上,看着那森林。看着那森林时,我想起了一个传说。传说中的白马鸡是英雄战神格萨尔的士兵,在格萨尔之后,它们化作白马鸡隐于山林。如果有一天格萨尔重新降世,开始新的征程,这些白马鸡身上洁白的羽毛就能重新变回银色的铠甲,赶往他的帐前听候主人的调遣。
老甘和我在那山梁上一边啃着干粮,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论着有关这座森林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在前20 年里,每年5 月至10 月的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山上伐木,每三五分钟时间就可以伐倒一棵树龄在200 年以上的大树。他手中的油锯在锯向那些坚硬无比的树干时就像用镰刀收割麦子一样容易。他一年至少要伐掉约1000 棵高大的树木,最大的一棵云杉树的木材估计会超过18 立方米,那得用好几辆大卡车装才能装完。20 年间,他至少伐倒过约3 万棵大树,而每年的春天,他又一直在山上植树,一天要种植约500 棵树,一个春天至少要种植约一万棵小树。24 年间,至少栽种了约30万棵小树。20 年以前,栽种的那些云杉苗长势最好的一小部分已经可以当椽子了。他说,算下来他种的树还是比砍掉的多。虽然砍掉的都是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而种下的树也得几百年之后才能长成原来的样子,但它们总会长大的。
在几次采访之后,当我又一次走进玛可河时,面对四面郁郁葱葱的青山林莽,不由得对玛可河林业人生出些敬佩来。尽管他们也曾大肆砍伐这里的森林,但那都是在“国家建设需要”的大背景、大计划下采伐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几十年不间断地实施人工造林、抚育幼林、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等生态工程措施。尤其自1998年天然林禁伐、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后,他们更是加大了天然林的保护和公益林建设。至21 世纪初,玛可河林区已还清以往所有砍伐造成的资源欠账,林木蓄积超过20 世纪中叶以来的最好水平。仅1998 年至2002 年的4 年间,玛可河林区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3468 公顷,封山育林35145 公顷,幼林抚育100 多公顷。几乎所有过去的采伐基地上都长出了新的森林。据赫万成介绍,玛可河林区借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东风,已然走上良性循环的绿色大道。
在告别玛可河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总会想起那片森林,想起那片绿浪翻滚的山野。每次想起玛可河的森林,我都在想,如果它从不曾被砍伐,一直保持着它原始的风貌,依然有漫山遍野的苍松古柏,那么,它又是怎样一派美景呢?虽然,玛可河的森林还在,却已经没有了漫山遍野的苍松古柏,而一座没有了苍松古柏的森林是否还是一座真正的大森林呢?
有一次去玛可河时,我专程去拜谒过那棵号称“青海树王”的古树,据说它是青海境内最高大的一棵树,生长于班玛县灯塔乡格日则村的哑巴沟里。据玛可河林业局局长韩才邦介绍,这棵树在民间传说中的树龄是682 年,估测树龄622 年,树高43 米,胸径1.28 米,平均冠幅13 米——东西14 米,南北12 米。此树为川西云杉,属裸子植物,松科,云杉属,川西云杉种,为浅根性常绿乔木,分布在海拔3300~4300 米的高山地带。球果紫红色,卵状长圆形或圆柱状,长5~11 厘米,花期5 月,球果10 月成熟。
在它身旁还分布有十余棵与之比肩的高大云杉,树龄大多在500 年以上,树高都在40 米上下。云杉乃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建群树种,远远望见一片山野透着黑黢黢光芒的就是云杉林。在低海拔地区云杉的生长高度可达45 米以上,这里的海拔已经超过了3500 米,这几乎是云杉在这等海拔区域的极限高度。站在一棵树下仰望,竟有眩晕的感觉。
这是极致对视觉的冲击,任何事物——尤其是生物的繁衍生长,一旦到了极致,人类的心理层面就会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感。我想,这是生物界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反应。如果有一天,人类心理学能推及整个生物圈,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最初神话与宗教信仰的产生就跟这种本能反应息息相关。也许是因为人和树木都向上生长的缘故,当一个人走进一片如云杉这般高大的乔木林时,一棵云杉所能达到的生长高度,在人类就成了难以企及的高度。站在一棵高大的云杉树下仰望,树梢上挂着流云,树头上顶着苍穹和日月星辰,想想,都会令人肃然。
我去的时候,离那棵川西云杉不远处的阳面山坡上有一棵高大的云杉倒在地上,应该是风倒木——这是一个专业术语,因为根浅,大树被风吹倒的事在云杉林中时有发生。我从它的根部位置上到树身上,向树冠走去,像走在一座独木桥上,而后站在树冠位置给它拍照。这是一棵自然死亡的大树,生生灭灭的事,在自然界原本就是常事。我想象过,如果它不是躺倒在地上,而是还在向上生长,一个人还能站在上面,沿着它粗壮的躯干一路走去,说不定就能走进天界。若如此,也许他就能听到从未听到过的天籁——也许还能听见众神的窃窃私语。对生命而言,那一定是一种无比神圣的体验,足以令其脱胎换骨,飘飘欲仙。
也许藏民族天生对这样的事物抱有敬畏之心。曾经的岁月里,很多生活在林区的藏人,身边到处是高大的树木,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间像样的房舍,只用类似风倒木——甚至只用树枝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小棚屋赖以栖身,而从不会将手中的刀锯伸向尚在生长、依然活着的林木。
这也许就是班玛那一片片碉楼的真正意义——有关这些碉楼的事,我将留在后文中专门叙述,不表。按说,在林区用木头建一座房屋要比用石头垒砌容易得多,林区盛产木料而非石头——石头必须从林区以外的地方搬运,这又是何苦呢?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珍惜所有能在大地上生长的生物,包括草木。
这些年,我不厌其烦地在重复一个话题,那就是生态伦理,一个将宇宙万物均纳入理论视野的伦理体系,我称之为天地伦理学或万物伦理学。其中,人类虽然仍居于重要位置,但已经不是中心位置,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宇宙万物得以存在延续的根脉。如果此体系有个边际,那一定也是大千宇宙的边际。简单地说,如果以大千宇宙的边际画一个圆,那么,它就是处在最外层的一个圆。这个圆里面有无数个圆,其中离中心圆点最近的一个圆就是生物圈,所有动植物都在这个圆圈里面,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少从数量上讲,它所占的比重只是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每一个圆都有自己的疆界限定,像天体的运行。每个圆既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也有整体的运行规则或规律,老子称之为“道”,不可随意逾越,否则就会对其整体结构造成威胁和破坏,最终殃及自身,甚至祸及圆点,而那圆点则是根本。如果整个体系是一棵树,那个圆点就是树根。此乃天条,是大道,亘古以来,天地万物均受此约束。回过头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先对此做出挑战并不断挑起事端的一定是人类——也许还有像人类一样的外星其他智能生物。
他们不甘心受到自身以外的其他约束,于是乎,不断越过界限,侵害到别的世界,继而对整体造成伤害。从人类所在生物圈而言,最先受到侵害并造成重创的就是动植物,之后是包括水体在内的矿物,之后是大地和天空以及空气……
这话似乎扯远了,就此打住。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班玛藏人对自然万物一直秉持的一种伦理情怀。
在哑巴沟口,清澈的小河边,有一道石墙,用片状石板垒砌而成,因为年代久远,石板缝里已经长满了青苔和各类花草,其中有几株野生的兰花和菊科植物。裸露的石板上也已经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硬壳,那是岁月的痕迹。我原以为,这石墙是以前一座房屋坍塌后留下的墙体,可是近前细看,才发现,它并非普通的墙体,而是一道石经墙,也就是说,那每一块石板上都刻有经文,内容都与慈悲有关。这是一堆承载慈悲的石头,这是一道慈悲的墙。世上所有的墙体都是用来阻挡某种力量的,而它不是,它的存在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安放心灵。石墙的垒砌者安放的是他自己的心灵,之后所有从这里经过、驻足的人,看到了,也可以安放自己的心灵。但是前提必须是,你要安放的也得是一颗盛满慈悲的心灵,否则,你永远无法安放。即便强行为之,也不会安妥。
离石经墙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片石墙。那里原本有几座房屋,房屋倒塌后,石头垒砌的墙体依然完好。石墙上有门,门里狭小的空间被葳蕤丛生的各类植物挤得满满的,竟还有一两棵高大的乔木,你要从门里进去,如同穿越一片丛林,得小心绕开那些枝枝蔓蔓。进去之后,我看到里面的墙体曾精心粉刷过,除靠门的一侧,其余三面墙上都有彩绘的佛像,每幅佛像都不大,大多与一片莲叶相仿,虽然有几尊佛像因墙皮脱落有所损坏,但所有佛像的色彩依然鲜亮。我无法断定这是一座僧舍还是普通民居,但其主人栖居于此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一个住在如此狭小的居所、却在墙面上画满了佛像的人即便是一个普通人,其心灵也绝不平凡。
在物质世界里,这自然是一片废墟,但在精神世界里,它又未尝不是一片净土圣地,乃至一座殿堂。
可以肯定的是,当初很多的班玛藏人是住在森林里的——其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依然住在森林里。藏族社会总体上可归结为草原文明的范畴,游牧文化是其最显著的标识,但也有特例,比如班玛藏人。除却一些高寒草甸牧场,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班玛藏人的居留之地仍有森林分布,属森林地带,有小片农田可耕作。而且,这些森林地带是藏地果洛最早有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果洛藏人的主体最初都生活在这里,班玛是三果洛不争的发祥地。可以说是班玛的森林哺育了果洛的文明。
后来,当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传入这些河谷森林地带时,这片土地早已为迎接它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于是草木森林焕发出神性的光辉,那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心灵感悟。因而,他们的生命与宇宙万物之间有了最直接的血脉联系,使天地万物连接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从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一条话语通道就这样打通了,鸟兽鱼虫、花草树木、浮云流水的世界与人类终于建立起可以相互沟通和交融的整体语境。如果说,往昔的岁月里他们也曾感觉到自己与大千世界某种不甚明了的血肉联系,那么,从此他们的心识世界就有了一个指引,借此他们可以妥善安顿自己的心灵。再看周围的世界时,一切都有了生命的气息。那山、那水,那天空和大地,那林莽、那参天大树,在他们眼中都成了神圣的所在,因之满怀敬畏。
之后,佛教文化也随之而来,它带来了慈悲。自然万物因之又有了慈悲的模样,人因之悲悯、感恩。世界因之归于安详。一切归于安详。
那天,午后的阳光下,立于哑巴沟口的那片废墟前,我再看玛可河那无边的林莽时,我眼里已全是慈悲的光芒。
一片森林的存在就是一种慈悲。如果你曾静静地坐在一片森林的边上,久久端详过一片森林,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什么。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任何时候,一片森林都闪耀着醉人的光芒。
无数阔叶或针叶的树木、开花或结果的植物,用每一片叶子和花瓣承接着阳光雨露,每一片叶子和花瓣都泛着细碎的光芒,像音符。微风拂过,温暖的、柔和的光芒又从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上弥漫开来,荡漾着,婆娑着,汇聚成无边的光芒。但从不炫耀,从不张扬,从不刺眼,而只是静静地、淡淡地、悠然地绽放,像微笑。因而任何时候,走进一片森林,你的身心都会受到一种抚慰。于是,你会顿时安静下来,从未有过的宁静在四面山野如丝如缕。那时,你会感觉,自己也像一株栖身林下的植物,灵魂深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摇曳,静静绽放。
我以为,那并不是花朵,而正是慈悲。
摘自《雪山碉楼海棠花:藏地班玛纪行》
热门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