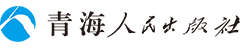千载识堤第一家
2023-11-02摘自《束与分的变奏:黄河治理简史》原文地址
千载识堤第一家
文/赵炜
潘季驯于堤防的贡献,突出的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尤其在理论上,他辨疑释惑,认识深刻,界定科学,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千载识堤第一家”。
首先,潘季驯对堤防的作用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分疏与筑堤之争,统一了思想,奠定了堤防在黄河防洪工程建设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明以前,尽管对堤防的作用以及建设、管理、养护、抢险、堵口等已有所认识,但由于受大禹治水、西汉贾让“治河三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考量,对堤防的存在价值争论不休,发展缓慢。特别在宋、元以及明前期的治黄主张中,甚至把堤防认为是导致黄河治理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并于明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流治河实践。
潘季驯是在分流治河遇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开展治河活动的。实践中,他认真总结、分析、研究历代治河,特别是当时治河的经验,针对黄河水沙特性,大力提倡通过堤防来达到“以水治水”的目的,从而赋予了作为重要防洪手段的堤防工程以新的意义,实现了从防到治,从对付水到对付沙这一堤防概念的根本变革。
分析潘季驯对堤防作用的认识,最早是通过对历史上一些错误观点的驳斥而展开的。如他把治水与筑堤完全对立的观点,归结为崇古思想和失之细考的片面解释;针对贾让等人的一些堤防观,他从堤防角度立论,把障与疏、宣与塞统一到堤防中。如潘季驯把遥堤、缕堤作为束水攻沙的工具;遥堤、格堤作为淤滩保堤的工具;顺水坝作为挂淤固堤,保护要害处所的工具;挑水坝作为辅助堵口的措施等。这些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论证、措施,当然也就会产生非常强的说服力。另外,潘季驯还把传统方法与现实方法统一于堤防中。他在《申明修守事宜疏》中说:“束水归漕,归漕非他,即先贤孟轲所谓水由地中行”“堤防非他,即禹贡所谓九泽既陂,四海会同”等。
当然,同时代人的影响也不能低估。工部尚书朱衡,曾两次主持治河,强调堤防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傅泽洪主编的《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一书中清晰指出“国家治河,不过浚浅筑堤二策”。万恭则从水流的特点,分析堤防的重要。他说:“故欲河之不暴,莫若令河专而深,欲河之专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骤,使由地中行,舍堤无别策矣。”万历二年进士、工部主事佘毅中也认为河绝不是堤防的过错,这一观点被记录于张希良所著《河防志》一书中。他说:“顾频年以来,无日不以缮堤为事,亦无日不以决堤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杂以浮沙而不能久,堤之制未备耳!是以河决崔镇等口,而水多北溃,为无堤也。淮决高家堰、黄浦等口,而水多东溃,堤弗固也。乃议者不咎制之未备,而咎筑堤为下策,岂得为通论哉!”
其次,创立了一整套完整而又规范的堤防制度,包括堤防建设的标准、规格,堤防的守险、减水设施、检查修补、紧急抢护及守堤和堤夫的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其所著的《两河经略疏》中,他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一是“堤欲坚,坚则可守,而水不能攻”,这是保证堤防安全的首要条件,尤其是导流、挑水堤段,更应经得起水流的冲刷;二是“堤欲远,远则有容,而水不能溢”,要求要满足过洪的基本要求;三是“凡堤必寻老土,凡基必从高厚”,从堤防的施工技术上提出要求;四是因地制宜地创筑遥堤,以增加防洪安全;五是“创建滚水坝以固堤岸”“则归漕者常盈而无淤塞之患,出漕者得而无他溃之虞”。总之,“欲堤之不决,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费,让远而勿与争地,则堤乃固”。
与之相对应,潘季驯还把堤防的修筑与防守提到相当重要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他首创了堤防的分类方法。如他按堤防的材料将大堤划分为土堤、石堤、砌石护坡土堤等;按作用分有缕堤、遥堤、挑水坝(导流坝)、丁字堤及落淤固滩的顺水坝,有些堤段上还视防洪要求修筑了溢水坝和滚水坝。他进一步强调堤防作用及经久稳固在于人而不在堤,并详细制定了一系列的堤防修守制度。如铺夫制度、大堤加固制度、四防二守制度(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官守、民守)、岁修工料准备制度、防汛报警制度等。所有这些,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也是较为科学而合理的。
第三,更重要的是,潘季驯的堤防实践。他第二次治河时,筑缕堤“3万余丈”。第三次治河时,“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明史·河渠志》)。第四次治河时,仅在徐州、灵璧、睢宁、邳州、宿迁、桃源、清河、沛县、丰县、砀山、曹县、单县等12州县,加帮创筑的遥堤、缕堤、格堤、太行堤、土坝等工程共计“十三万多丈”;在河南荥泽、原武、中牟、郑州、阳武、封丘、祥符、陈留、兰阳、仪封、睢州、考城、商丘、虞城、河内、武陟等16州县,帮筑创筑的遥、月、缕、格等堤和新旧大坝多达“十四万余丈”。据《河防一览》一书中粗略统计,潘季驯三次治河,总计筑堤达1300多千米。
好的理论,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潘季驯第三次治河后,十余年未发生大的决溢,行水较畅,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如太仆卿常居敬在《钦奉敕谕查理黄河疏》中说:“数年以来,束水归槽,河身渐深,水不盈坝,堤不被冲,此正河道之利矣。”太常卿佘毅中在《全河说》中也说:“今太子少保潘公,屡膺河寄,洞炤委源,才諝精诚,并称绝世……故自告竣以来,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并力以推涤海淤,而海口之宣泄二渎也急。用是河尝秋涨而涯畛屹然,淮尝夏溢而消耗甚速。贡赋舳舻,若履枕席,转徙孑遗,寝缘南亩,盖借水攻沙之效已较然显白矣。”在第四次治河时,他大规模修筑黄河下游两岸长堤,巩固堤防,河道基本趋于稳定,扭转了嘉靖、隆庆年间河道“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明史·河渠志》)的混乱局面。这些成就是同时代的任何人所未达到过的。
潘季驯在堤防建设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与其对黄河水沙特性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如他抓住黄河“水少沙多”的特点,得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等关于水沙关系的科学论断,与现代河流动力学中水流挟沙力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的黄、淮、运关系与黄河河道,他提出了稳定河道、坚筑堤防,束水攻沙、借清刷黄的治河方针是颇具见地与合理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其理论的局限性。由于过高地估计了“以水攻沙”的效果,过分强调水流对河道泥沙的冲刷作用,忽视或讳言泥沙在黄河下游淤积的不可避免性。另外,其理论仅对下游河道做文章,而未意识到对上中游沙源的控制等。正因如此,潘季驯主政黄河治理时期,并未达到其理想中的效果。
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和堤防观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清初著名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在《禹贡锥指》一书中盛赞潘季驯:“观其所言,若无赫赫之功,然百余年来治河之善,卒未有潘公者。”清代治河专家陈潢在《河防述言》一书中指出:“潘印川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说,真乃自然之理,初非娇揉之论,故曰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近代治河名人李仪祉及一些国外治黄研究者对潘氏的理论也颇为赞赏。在人民治黄的今天,黄河下游的堤防经过70余年不断建设,已初具规模。重视堤防,加强人防,“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等治黄方针,也无不与潘季驯治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有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下游堤防建设的投资力度日益加大,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堤防工程更加完整、坚固,充分体现了潘季驯坚筑堤防的思想。
摘自《束与分的变奏:黄河治理简史》

热门排行